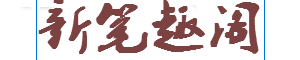第十七章 求才若渴(1/2)
作品:《我欲扬明》东暖阁里,朱厚熜微笑着对行礼如仪,被赐坐的李春芳说:“李阁老,朕批转给你和曾部堂的那份策书,你可看了?”
李春芳屁股刚刚落定,闻声忙又站了起来:“回皇上,臣已奉谕恭读完毕.”
“坐下说,坐下说。”朱厚熜迫不及待地问道:“写的如何?可有可用之处?”
李春芳叹道:“此策书上合兵法至理,深契当今时势,层层剖白、字明晰,实为实用适用之佳作。臣恭请皇上颁赐兵部并转南直隶、浙、闽等省依策施行。”
“哦,你真这么看?”
李春芳迎着皇上质疑的目光,语气坚定地说:“臣万死不敢欺君。”
“曾部堂怎么看?”
“臣曾询问过曾铣,他的看法与臣并无不同。”
“那就好!”朱厚熜吁了一口气:“朕此前曾听戚继光说过,此策所提方略十之可行,朕还以为他是率性浮夸之说,如今看来,倒真是治兵备倭之良策啊!”
原来,接到吕芳送来的徐渭那份论东南备倭御寇方略的《靖海平倭策》之后,朱厚熜压根也没有想到徐渭那个历史上有名的书法家、画家竟然也懂军事,加之徐渭为求打动当道,策书写得字古奥,用典考究,旁征博引,纵论古今,洋洋洒洒近万言,不但古功底不佳的朱厚熜看得糊里糊涂,就连御前侍奉墨的大才子张居正也因对兵法没有研究而看不大懂。兵凶国危,不可不慎,因而朱厚熜只是笑着说了句:“秀才谈兵,不务正业。”便将那份策书搁置案头。谁知过不多日,戚继光自宁波军前上呈急奏,声言此份策书所提方略都切中时弊,恳请皇上即时颁旨允行。朱厚熜这才知道,自己出于习惯性的思维定式,险些将一个旷世奇才埋没草野,更险些误了军国大事!不过,为了慎重起见,他还是先把徐渭那份纸上谈兵的策书批转内阁和兵部,让那些专业人士先审阅。过了几天,他就按耐不住好奇之心,召见了内阁分管军务的次辅李春芳,专门过问此事。
见皇上喜出望外,李春芳也凑趣说:“臣嘉靖十五年便任兵部尚书,入阁之后也掌军务,至今已逾十年,却还未曾见过这样说理透彻、分析明晰的兵备之策,可堪与曾铣当年《议复河套疏》相提并论。臣原本还以为,能做此书者,必不出俞大猷、戚继光二人。听皇上方才所言,竟还另有其人。臣恳请皇上将此人调职兵部,扬其所,参赞军机。”
朱厚熜脸上的喜色顿时不见了,眉宇之间现出了一丝忧虑:“李阁老有所不知,朕也正为此事犯愁呢……”
李春芳试探着问道:“莫非,此人是去年江南逆案中人,骤然赦免并调任兵部要职,恐招人物议?臣以为,如今朝廷正值用人之际,所谓大行不必细谨,大理不辞小让,为国用贤,不必计较过去。皇上推赤恩于天下,必定天下归心……”
朱厚熜叹一声:“唉!若是如此,倒也好办了。可惜此人并非朝廷职官,还只是一个布衣,又如何能在兵部任职?朕若下诏授官,岂不又招人物议,更有损他的清名雅誉?”
皇上说的这样恳切,李春芳自然唏嘘不已,但他也知道,这事确是十分棘手。大明官场频起大狱,朝廷命官动辄得咎,因此致仕还乡、乃至下狱充军都是寻常之事,除了京察被斥退的官员按例永不叙用之外,其他罪员一道恩旨便能起复。但这只限于在吏部记名建档的进士、举人,包括现任职官和候任官,《明会典》载有明,一个布衣百姓不经科举中式,是不能封授官职的。只有到了成化初年,登基不久的明宪宗命太监传旨封授一位工匠为思院副使,开了极其恶劣的皇上亲下诏命封授官职的先例,继而愈演愈烈,一些趋利之徒便借进奉之命,通过进献书画、玩器、丹药、方术等谋求一官半职。宪宗也是来者不拒,动辄传旨授官,将朝廷名器随意授受,更将大明官制、朝廷尊严践踏无余,引得朝廷重臣、科道言官,乃至外省督抚纷纷上疏抗谏,那些靠进奉得官的人武士、工役僧道之流更被官场士林讥讽为“传奉官”。至孝宗即位,就将多达两千余人的传奉官尽行裁汰。不过,虽说此例一开,就成为皇上的特权,尤其是正德、嘉靖年间,这样的事情也就屡见不鲜,但那都是皇上率性而为,让他这个内阁辅臣提出这个有违大明官制的建议,则是万难说得出口的。
犹豫了一下,李春芳才说:“观其策书,此子实为国朝罕有之贤才,臣敢问皇上一句,缘何却还未有功名?”
朱厚熜突然不高兴了,没好气地说:“你问朕?朕还想问你呢!”
李春芳闻言一震:莫非此人便是皇上以之作为增开时务科的理由,并有意要自己举荐入画院供职的那个浙江举子徐渭?大明子民数千万,生员也有好几十万,该不会有这么蹊跷的事吧?
还在心存侥幸,就听到皇上冷冷地说:“浙江政王开林是你向吏部举荐的吧?闻说还是你的乡谊?”
李春芳吓得一激灵,忙起身离座跪了下来:“臣无识人之明,妄荐庸才,贻误国事,请皇上恕罪!”
朱厚熜又将语气缓和了下来:“不必如此惶恐,始作俑者不是王开林,更不是你,倒
本章未完,请翻下一页继续阅读......... 我欲扬明 最新章节第十七章 求才若渴,网址:https://www.xbqg9.net/22/22892/377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