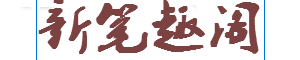第39章 舌战群戎(3/8)
作品:《恋千年》匿王的护持,佛教才能传遍五印度;佛陀灭度后,阿育王修建八万四千座佛舍利塔,并派遣布教师到锡兰等地弘法,使得佛教得以向外弘传,广宣流布。中国因有东汉明帝派遣郎中蔡愔西赴天竺迎请迦叶摩腾、竺法兰等高僧来华弘法,佛教因此得以传入中国。至于中国佛教的译经事业,大多是由于历朝帝王保护,设置译经院,因而得以完成,如鸠摩罗什大师受后秦?姚兴的护持,在西明阁从事译经,而有《法华经》、《中论》等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经论流传后世;玄奘大师在唐太宗的支持下,译出《大般若经》、《成唯识论》等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经论,使法宝圣教的光辉普照于中国。
佛教与政治的关系,可以说有如唇齿相依,关系密切,因此若问佛教徒可以从事政治吗?答案是肯定的。观世音菩萨以三十二应化身游诸国土,度脱众生,其中即有国王、宰官、大将军身,以其政治背景,为众生创造富足安乐、无有怖畏的人间净土。佛陀为国王们讲说转轮圣王的理想政治,乃至历代国师以佛法的智慧辅佐帝王治理国家,在在证明佛教徒可以参政,但不必直接干治的中道思想。
也就是说,我们应该保有‘问政不干治’的态度,但是如果有佛教徒参与政治,其实也没有不对,现代社会应该要有雅量接受,不能剥夺佛教徒乃至僧侣关心国家社会的权利,因为出家是信仰,参政是人权。
至于佛教徒能否参战?其实佛教本来就有在家与出家二众,即使是出家的比丘也有服兵役的义务;既然服兵役,国家是大我的生命,是众人所依,为国捐躯,为国牺『性』,为国杀敌,为国而战,不管在法律或舆论共识上,都会有公论的。
就是在佛教也有所谓的‘三聚净戒’,包括了摄律仪戒、摄善法戒、饶益有情戒,其中饶益有情戒是属大乘菩萨戒,所以佛陀在因地时为救五百个商人曾杀一个盗匪,这种为慈悲救人而杀,为饶益有情众生而杀,不是为瞋而杀,好杀而杀,非一念之仁,片面之仁所能比拟的。同样的,佛教徒参战杀敌,他不是为瞋恨而杀人,而是为尽忠报国,为了救生民于水深火热之中,如此救国救民之举,绝非『妇』人之仁可喻。
再说,国家战争也不全然是残杀无辜,有的王师之军是为了惩罚坏人、暴徒,有的救人于水深火热,有的保家卫国,在战争中也能表达仁爱、慈悲,在战争中更能发菩提心,行菩萨道,救济伤亡。
当然,战争是不得已的手段,非到必要时最好能用其他的方法,例如和平、道德、感动的力量都远胜刀枪。在中国的三国时代,诸葛亮”七擒孟获”,他知道杀一个孟获容易,但还会有无数个孟获起来反抗,所以用感动的力量才可以让人心服。
其实,佛教徒在修行的过程中要降魔,降魔就如战争,每个人内心里也有八万四千个烦恼魔军,也要降魔,也要战争。至于现实生活中能否参战?这就要看自己的人生观,如果是小乘修道者,小乘人要求消极的慈悲,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杀生,这当然是好事;但大乘佛教主张在必要时,应该以力量折服敌人,也有需要。所以参政、乃至参战与否?就看自己是发小乘的自了心,还是行大乘的菩萨道而定了。
总之,人本来就是政治动物,关怀社会则不能不关心政治,政治是管理众人的事,人是群众动物,无法离群索居,势必与大众有密切关系;既然无法离开群众,自然不能远离政治而生活。所以,佛教对于社会的关怀、人权的维护、民众的福祉,自是不能置身事外,当然也不能以远离政治为清高,所谓”问政不干治”,个人可以不热衷名位权势,但不能放弃关怀社会、服务众生的责任。也就是说,今日佛教徒为了弘法利生,对政治不但不应抱持消极回避的态度,相反的,应该积极关心,直下承担,这正是人间佛教菩萨道的实践。”
耶律水墨还想为难王木木,就说:“请问大人,现在举世天灾**不断,有人说这是人类杀业太重的果报。请问大师,佛教慈悲戒杀的教义可以改善社会风气,甚至转变人类的共业吗?”
王木木回答:“佛教讲因果业报,每个人投生到世间为人,除了依个人的三业善恶好坏,感得的正报有智愚、美丑、高矮、胖瘦等差别以外,众生共通的业因则能招感自他共同受用的山河、大地等器世间,这是依报的业,称为共业。
业,就是行为;行为的善恶可以招感各种祸福。一个人在生活中因”别业”与”共业”而遭遇的灾难,大致有自己招感而成的”自灾”,如疾病、残障、失业等;因人制造出来的”人灾”,如绑票、贪官、杀戮、中伤、毁谤等;由大众共业所成的”共灾”,有大自然的风、火、水、旱、震灾,乃至战争、虫害、瘟疫等天灾**,这些大家共同感受到的灾难,就是众人的业报所招感,称为共业。
记得有一次我在哈佛讲演,有人希望我具体说明佛教对于国家、社会能提出什么贡献?当时我说,举凡三藏十二部的圣典,都可以有益于国家社会。简单地说,只要一个五戒,就可以治国平天下。
五戒就是不杀生,不偷盗,不邪『淫』,不妄语、不饮酒。现
本章未完,请翻下一页继续阅读......... 恋千年 最新章节第39章 舌战群戎,网址:https://www.xbqg9.net/7/7707/37.html